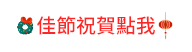就在媒體報導泰勒絲(Taylor Swift)成功談判,悄悄買回她早期六張專輯的母帶版權之際,這位流行樂壇巨星再次顛覆傳統音樂產業遊戲規則,證明她不只是創作才女,更是當代最精明的文化創業家之一。
根據《富比士》估計,年僅35歲的她,已是史上首位主要靠音樂創作與演出累積超過16億美元財富的女性音樂人,是碧昂絲(Beyoncé)財富的兩倍以上。在串流主導、權利碎片化、唱片公司掌控的年代,泰勒絲挺身重寫遊戲規則——不只是為了自己,也為整個創作世代。
從權利被奪到買回版權:一場策略性的逆襲
2025年5月30日,泰勒絲向她的廣大粉絲宣布了一個好消息:「我創作過的所有音樂,現在都屬於我自己」(All of the music I’ve ever made now belongs to me.)她證實已以近3.6億美元從Shamrock Capital手中買回2006年至2017年間前六張專輯的母帶與附屬版權。這場母帶買回之戰起於2019年,當時音樂經紀人Scooter Braun透過收購Big Machine Records而間接取得她的錄音母帶,未與她協商。泰勒絲當時表達強烈不滿,並拒絕「被迫沈默」。
但她選擇不靠法律戰,而是另闢蹊徑。她啟動名為「泰勒絲版本」(Taylor’s Version)的重錄專案,將原有六張專輯逐一重製且重新發行,並號召粉絲只聆聽她重錄版本。此一有勇有謀的對抗行動,最終成功地讓原始母帶貶值,重錄版在串流與實體市場雙雙勝出。誠如《哈佛商業評論》資深編輯凱文・埃弗斯(Kevin Evers)在其新書中所說,「這不只是重錄專輯,而是奪回定義權與話語權的過程。」
從音樂人變成品牌操盤手
若說泰勒絲的成功只是情感勝利,那將大大低估了她背後精細的策略設計與財務智慧。湯明哲與謝凱宇在一篇專文分析中指出,泰勒絲之所以能快速累積財富,關鍵之一在於她善用「差別取價」策略——她將不同支付意願的粉絲分層,讓高價值粉絲先行消費,並延後開放低價或免費模式。
2014年,她新專輯《1989》發行時,要求Spotify延後上架半年,且不對北美用戶開放免費串流。被拒絕後,她毅然將作品全數下架,改與Apple Music簽下獨家合約。直到2017年,泰勒絲才重返Spotify,仍堅持新專輯發行後兩週內僅限付費用戶收聽。
正如湯明哲與謝凱宇所分析的,這正是經濟學上的價格歧視邏輯:先向支付意願高者收取較高價格,再逐步開放低價或免費的發行渠道,以達成收益最大化。她不僅運用這套邏輯在音樂銷售,也將之延伸至演唱會售票與授權模式,包括讓信用卡公司競標最佳座位權利,甚至讓新加坡政府付出數百萬美元取得東南亞唯一場次。
粉絲是資本,不只是聽眾
泰勒絲在這場主權逆襲戰中,最強大的武器不是律師團隊,而是她的粉絲群體。她沒有靠串流平台發動聲量,而是將自身品牌轉化為一個可共同參與、解碼、二創的文化共同體。她透過彩蛋、MV隱藏訊息解謎活動、社群任務與解鎖機制,讓粉絲不只是支持者,更是敘事共創者與品牌行動者。
在這本《獨一無二的泰勒絲:流行天后的策略天才》(There’s Nothing Like This: The Strategic Genius of Taylor Swift)的新書裡,埃弗斯描述泰勒絲如何「將個人故事與音樂編織在一起,並引導聽眾在社交媒體上擴展這些故事」,使粉絲成為整個泰勒絲「故事宇宙」的一部分。埃弗斯強調她「不僅適應了數位環境,更塑造了它」——泰勒絲不只是發行專輯,而是讓粉絲成為品牌經濟的共同產製者。這也解釋了何以她能動員全球數以億計的聽眾,將「泰勒絲版本」推上音樂排行榜,進一步鞏固她奪回母帶的談判籌碼。
埃弗斯也在書中強調,泰勒絲從不依賴所謂的「天賦自然」——她深知「自然」的表現往往是舞台上最不自然的表現。她投入極大時間與團隊資源訓練說話、走位、眼神與聲音,甚至如同運動員般排練每一場演出與訪談。她塑造的不只是風格,而是一套可以與資本抗衡的敘事結構、一種制度空白中的替代實踐。
而這些,正是泰勒絲與其他音樂人最大的差異:她不只是創作、表演,而是建立一整套可重複、可擴張的個人品牌主權系統——涵蓋創作控制、價格主導、粉絲互動、議題設定與媒體節奏掌握。她既是創作者,也是制度設計者。
對文化創作者的啟發
泰勒絲買回母帶與其品牌策略,不只是歐美音樂產業的鮮活案例,更可提供全球創作者與文化政策制定者參考。
台灣創作者經常陷入受制於人的困境。無論是音樂、劇集、Podcast還是YouTube內容,若無法掌控平台、版權與再授權的遊戲規則,創作的價值終究被分割成「看似屬於自己、其實無法支配」的泡影。
泰勒絲用她的行動提醒我們:創作者不能只是「內容提供者」,更要成為「制度參與者」與「品牌設計者」。否則,一旦被捲入平台規則或資本操作,連自己寫自己唱的歌,也會變成別人的財產。
泰勒絲說過:「我想擁有它;我為此而戰;我理所當然地贏回它。」(I wanted ownership. I fought for it. I earned it.)
這不只是情感敘事,更是一種制度主張,示範了如何不再輕易被資本邏輯主導的產業遊戲規則所擺佈。在這個創作者頻繁被平台邊緣化、被資本操縱的時代,她選擇透過策略、粉絲、議價與品牌設計,一步步奪回屬於自己的權利。她買回的,不只是錄音母帶,而是一種創作文化主體性的自我重建。